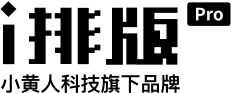HAKUCHI將於2026年初改名「以幻除幻」!我們準備了「HAKUCHI紀念禮包」,含有諸如過去展覽的海報和門票、印銀的Print和卡片、絕版的報紙、貼紙、紋身貼等物,數量都很有限,每個禮包將隨機放入七種。即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在HAKUCHI商店中單筆消費超過300元,可以獲得一份禮包。
●
牧野俊介
當時29歲
86歲時畫
「廣島核爆救援活動」
電車裏有人站著,也有抱著嬰兒的母親。多則二十幾人,少則五、六個人。車廂內漆黒一片,進去能聞到瀰漫的異臭。
牧野俊介
當時29歲
92歲時畫
廣島西部。小學生被埋在倒塌的校舍下,許多生命逝去。祖母大概是找到了自己的孫子,抱著不放,一直哭,直到天亮一起死在那裏。
牧野俊介
當時29歲
92歲時畫
河裏漂浮著太多馬匹,我向一位被爆者詢問後得知,原來是上游練兵場裏的馬弄斷了繮繩,翻越堤防跳入河中。人類會被火化,但馬卻順河著漂流到海裏,成了魚的食物。真是可憐。
山田須磨子
當時20歳
50歲時畫
八月七日上午十點左右,我和弟弟走得很累,從被燒過的水管那裏喝水。喝下那紫色的生的溫的根本不算水的汁。
非常噁心但是不得不喝。
煙霧籠罩,屍體還是昨天的樣子。胸口非常沉重,兩個人互不交談,默默走著。此刻我一邊追思亡故的弟弟,一邊流下新的眼淚。
當時23歲
53歲時畫
八月九日下午三點左右。在流川的電車通北側有一個水槽,水槽裏長長的黒髮鋪滿整個水面,仔細一看,底下好像有人坐著。我不由得打了個冷顫。
壷井進
當時17歲
八月六日下午兩點左右。盛夏耀眼的太陽曝曬著的酷熱時分。從鷹野橋向高須走著的我,在住吉橋上看到一個婦人擡起臉來求水。那張臉因為燒傷而腫得很大,眼睛和嘴巴看去都只能算是小洞。
不知道她是在何處被爆的,她應該無法在熱天之下、燒灼的道路上(橋)移動了吧。她苦苦求水、求我把她扔到河裏去,但我什麼也做不了。核爆帶來的燒灼、把城市燒盡的猛火、盛夏的酷熱⋯⋯逼人求水,跳到市内流淌的的七條河流和眾多防火用水槽裏,死在其中的人有很多。
恵下計一郎
當時29歳
寄贈者 恵下弘文
當時我家有六個人,經營小吳服店的父親、母親とし子、我(當時三歲)、剛來到世上的妹妹和祖父母,住在玖波(現在的大竹市)。父親在私人經營之外,應該還在機關裏幫忙。我幾乎沒有被爆時的記憶,只是通過父親留下的親歷紀錄「被爆者の叫び 大竹市原爆被爆者協議会」和不時跟我說起的親身經歷來了解。特別是沒有他因為原爆症而煩惱的記憶。父親從二十多年前起因為興趣開始畫油畫,去世前五六年還在畫風景畫。我不曾一睹父親的工作室,過了三十歲我上小學的兒子跟我說過「爺爺的房間有可怕的畫」,我想就是這次寄贈的這幅畫。我的父親從近二十年前起就一直畫這幅畫,最後沒能完成。
小川紗賀己
當時28歲
約58歲時畫
一、因炎魔而無處可逃的人們全都一起在防火水槽裏變成被燒者屍體的盛花【註:花道用語】
二、水槽外的黒色只是白骨上覆蓋了炭
三、小的屍體是小孩,五十釐米左右
四、到了第三天被燒者屍體變成紅色,就像赤鬼的樣子,看到就不由自主轉過臉去
高橋昭博
當時14歲
42歲時畫
8月6日上午9點前後,市內的操場被爆,從那裏逃往太田川。
我和友人一起逃跑。那位友人腳的內側被火燒傷了,沒法行走。有時候四肢著地爬著、有時候扶著我的肩逃命。我們逃到橫跨太田川的木橋的瞬間,那一帶竄起火焰。我們拼命逃跑。
小野木明
當時15歲
45歲時畫
從倒塌的房屋中,好不容易爬出來,最先遇到了鄰居大叔。他的雙手的皮膚整片剝落,只在指甲處還掛著。他拼命地去尋找孩子,但是孩子和他都死去了。畫中的表現絕對沒有誇大。
河野寛治
當時23歲
81歲時畫
[...]
【前文寫到作者被倒塌的建築壓住,死命逃出】這時外面通紅的火大範圍熊熊燃燒,火情很嚴重。到處都是四散奔逃的人。我也跟著人群,不知道去哪、不知道怎麼走的,就進到了河裏(天滿川)。有不知幾百人進到河裏,有許多人死掉後橫浮在河面,隨後我混在幾十列逃亡的人裏沿著電車道走著,一起向西逃。
總之我只顧著拼命逃,完全不知到底身在何處。看到被火燒的房子下埋著的人也無能為力。到處都只能看到在火中奔走的人,渾身是血的、皮膚剝落全身露出赤紅色肉的、眼球掉出來的、嘴唇腫得巨大的,完全不是人形而像是怪物。好像每一個人都受傷了,其中有些人走不動就原地四仰八叉地躺著好痛好痛地叫喚,很多人在哭號,亂七八糟的,我在哪、是怎麼走的我現在都不知道。然後我和人群走散了,在安藝女校的田地裏坐下,橫躺下。
傍晚將近,這裏有許多不得不露宿的人。夜裏四處都還能看到火在燃燒。人群中到處有接連不斷的「水」「水」和「給我水」的悲鳴,但根本沒有水。許多人就這樣被見死不救地放任著次第死去。就算是現在,無論怎麼想都還覺得那是人間地獄。夜裏也無法入睡,很難受。旁邊的人也接連死去,到底有幾十人我也不知道。在田地或野地中一個個死掉。我做不了任何事,只能哭泣。天亮時候大部分人已經不在了。我想是因為死的人太多,而且有些人不知逃去哪裏了。我把草扯下來塞進嘴裏,但是草太苦吞不下,又吐掉了。隨後人們又一個個慌忙逃竄了。
我沒法去我家那一片,只能等火熄滅。第一天第二天我到處徘徊。因為沒能遇到熟人,第三天我朝廣瀨方向繞到了三瀧那邊,往橫川站的方向走,終於來到鷹匠町我家所在的地方。到處都燒得面目全非,我尋找著高木的紅豆湯店所在的地方。在完全不辨東西的火勢中,到處都還在燃燒,熱到無法通行。第三天十點,我找到了被燒完的家所在的地方。親哥哥、親姐姐還有三天前生下來的男嬰(三人)一起被燒了。為了把那些骨頭帶回,我移開大約一尺五寸的土(瓦礫),把骨頭撿走。家周圍,警防團的人和士兵將被燒的人收集,在路旁有好幾處地方集中堆放被燒者的屍體。是男人是女人,哪是哪誰是誰都無法分辨,都被燒得焦黒。我合上掌,只是不停念南無阿彌陀佛,眼淚流了出來止也止不住。
火每天在廣島的街上燃燒,持續了一星期以上。幾百個中學生為了進行清退、疏散的社會勞動排成一列,就那樣幾百個人並排著死掉了。我看到那場景眼淚止不住地流。一邊哭,一邊說著對不起、對不起,跨著屍體走了過去。似乎都是比較完整的屍體。一星期左右屍體腐爛了,炎熱的夏日裏,被隨意棄置的死去的人們,那肉裏的血和脂肪的極強烈的屍臭,讓人難以呼吸。蛆蟲孳生,從傷口裏鑽出來。接著它們變成幾百隻蒼蠅,黒壓壓的,看著也令人難過。幾十人的屍體被一直一直放著。人們只是倉皇逃跑,沒有一個人處理屍體。漸漸肚子餓了,還是要去找些能吃的。一無所獲時有士兵給了我三個飯糰。那時我說了一句「對不起」。飯糰我沒有馬上吃,而是帶著,不知道能保存幾天。我非常擔心家人,到處尋找,從別人口中我才知道他們果然是四散逃走了。接著下起了雨,黒色的雨,淋濕全身,像被塗上黒色的墨,髒透了。我撿來被燒過的鐵皮,蹲在裏面忍耐著。雨時落時停。【註:黒雨是廣島核爆往事的象徵之一,是「放射性降下物」,由核爆後的雜質、放射物等構成,油膩、黏稠】
綿岡順次郎
當時46歳
75歲時畫
到了第五天,全身腐爛的屍體終於浮上來,像被大菊花覆蔽般。強烈的惡臭讓人停止呼吸。
横山義久
當時32歳
約62歲時畫
為了工事爬上電線桿,大概在手剛碰到電壓器的達摩形絕緣礙子的瞬間,原子彈就投了下來。
泉原寅男
當時23歲
中午前,從爆炸中心地帶附近往東到京橋川,從事修復作業的我們在東練兵場附近吃午飯。休息了一會,我們穿過榮橋去繼續作業。突然我們看到兩具人骨橫躺在橋床上。在河的正中,沒有火燒痕跡,為什麼會被燒成骨頭呢?我很疑惑。稍微走在前面的人只是碰了一下骨頭,那之間,最多大概兩三秒,骸骨從腳尖到天靈蓋全部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了,乃至兩具都一起完全化成了灰。我畫這幅畫是想大家知道,下落不明的人中有些就像這樣消失了。
松室一雄
當時32歲
61歲時畫
竹屋小學校的一部分圍牆上,用燒焦的炭寫著要找的人的名字。
西村久子 你在哪裏 告訴我——媽媽/和子 一定要來這裏/三谷俊江平安/増田一平 みよ子平安去向原了/爸爸媽媽都沒事 來比治山御便殿 三戸孝一/松田俊治 春子平安/川崎アキヨ 爸爸去吉田了/修治 來牛田/村上ヨシコ人在哪告訴我——母/去比治山 吉本圭次/伊藤みよ子 父母在比治山/久子 信一 來五日市——爸爸/圭一你在哪——媽媽 みよ子/吉田老師 保夫在哪裏——西田/君子告知所在——母-良枝/美代子美代子美代子告訴我——吉田/小松久人你不用擔心來馬上來五日市——野坂/忠 要活著 父母平安 在災墟等你/吉村健一平安去廿日市/知道佐々木昭信在哪的人請告訴我——吉本/浜井正子浜井正子浜井正子浜井正子/久保田悟人在哪告訴我——西条、三上/三戸良一/本本みどり/幸子 在等你 快來——向宇品父一郎/大塚三郎、光江 知道的人請告訴我——母信子
道岡クニ子
當時50歳
[...]那天傍晚,一冊被燒過的、破爛的『源氏物語』被扔進我家院子裏。無論如何也要抱走這一冊書的人、大概在避難途中力盡了吧。留下這一冊『源氏物語』的人今何在?
尾崎稔
當時13歲
尾崎稔
當時13歲
81歲時畫
安藝郡坂町鯛尾被爆者收容所,昭和20年8月7日夜半。有個少年大叫「我要成為特攻隊(神風特別攻擊隊),一定要打敵人!!」
8月7日夜半,一名少年突然直挺挺站起來,開始絕叫。片刻又啪嗒倒下去(生死不明)。他叫的內容是「我要成為特攻隊(神風特別攻擊隊),一定要打敵人」。周圍一片寂靜,但景象是地獄般悲慘的。在恐怖與不安中,少年強烈的不甘,我想一定有人感同身受。當時的事,即使過了70年我也忘不了。
山下正人
20歳
山下伍,二十歲。八月一日入伍第二部隊,八月六日在土橋的疏散作業中被爆。房屋被爆炸氣浪沖垮,當時他在二樓,身體翻滾著掉了出去。那天晚上和二葉之里附近的許多被爆者一起過夜。八月七日,步行返回小屋浦的途中在坂町植田倒下,被鯛尾的船舶部隊帶走。八月二十日回家,體力已經恢復到了能走路的程度,但是二十五日開始流鼻血、掉頭髮、全身開始長紅色的小斑點。八月三十一日吐著血死亡,在意識仍然清醒的情況下。
甲田敏春
當時12歲
69歲時畫
描繪原子彈(ピカドン【註:原子彈的日本俗稱,「ピカ」指閃光,「ドン」指爆炸聲】)投下的圖,表現的是藁葺屋頂的屋內、因圍爐裏的煙而昏暗的地方在一瞬間光束的光下通亮,一人驚駭的表情。這表情來自我本人,甲田敏春。
西岡誠吾
13歳
「冰涼的橘子」
【註:場景為收容所內】
下午三點左右,士兵分發給每位被爆者一個橘子。拿到橘子的被爆者中,驚訝和感謝的聲音在擴散。
橘子那冰涼的表面附有薄薄的冰。皮又薄又軟,一口吃下去又甜又涼,味道很新鮮。那時的味道我至今都忘不了。這些橘子是宇品陸軍糧秣支廠(負責採購、供應士兵的食物和軍馬的飼料的設施)分發的。
我躺著的地方旁邊有四、五個大叔在小聲說話。
「這次,長崎會不會也被像廣島一樣的新型炸彈炸得全滅啊?」「聽說蘇聯要發動戰爭,好像要攻進滿州了。」「日本會怎麼樣呢。咋辦呢。」「日本一定會輸啊。」
在曉部隊的兵舍,他們是從哪裏獲得這些情報的呢,真是令人費解。
聽到這些話,我變得很不安。
美味橘子的味道一下子被毀掉了。給戰局帶來不安的言行會受到嚴厲處罰的時代,大叔們警惕周圍,小聲地交談。
田中常正
當時25歲
55歲時畫
【畫面中】
「死之街 廣島的夜景」
一直在燃燒但已無物可燒的街上
火焰或熊熊或騰騰⋯⋯
直徑約三米,高大概有一點五米吧?
純藍色的火好像冒著聲音般地燃燒
到底有多少被爆者屍體在這裏燃燒啊⋯⋯
災墟成了小山,彷彿能聽到下方傳來呻吟聲
那應該是原西練兵場的一角,憲兵隊所在的地方
【背面】
我們在原子彈投下後第三天收到修復廣島的命令,中斷當時在山口的駐屯地秋穗二島的演習,前往廣島
清早在己斐站下車,前往中心地區設營
但是連煮午飯的柴火都沒有,不得已只能這裏那裏地在屍體焚燒場收集沒有燒盡的柴薪,終於把茶煮上、把飯炊上
澡桶的話,物色了沒壞的五右衛門澡桶【註:一種簡易的澡桶,將桶架在火上】,放在一直放著水的水管附近備用
但是太陽一落下天色變暗的話,野澡桶附近的瓦礫下埋著的腐爛屍體會發出青白色的火,誰都不敢入浴
白天,人們擔心自身和親友的安危四處奔走;到了夜晚街上活人的身影突然都消失得一乾二淨
屍臭在廣島的夜空瀰漫,夜夜難以入眠
[...]
小林岩吉
當時47歲
78歲時畫
六日夜/我枕著公會堂建築物疏散後的遺跡昏昏欲睡/忽然睜開了眼看到前方明亮 火球飄飄然地浮起 又緩緩落回/人魂在燃燒/所有的人魂都閃閃燃燒著/天亮時火球仍燃燒著/周圍有許多燒死者的屍體疊在一起倒著/合掌
【註:人魂,指鬼火、磷火】
渡慶次恒徳
當時29歲
屍體的臉、手、足全都像櫻島蘿蔔一樣膨脹、慘白。看著填埋河面的屍山,恒德被身體深處襲來的無力感侵襲。無論從河裏撈多少屍體都沒有盡頭。救護隊員們感到困惑。團員們統一了意見,不如先清理出能讓卡車通過的道路,於是在中午之前就停止打撈屍體了。
[...]
——宇多滋樹『豚の神さまー渡慶次恒徳の半生』
木村秀男
當時12歲
草津國民學校高等科一年級的木村秀男(當時12歲)在建築物疏散作業中被爆。那一瞬間,他被摔在地面,失去意識。當他醒來時,頭頂已被濃黒的煙霧覆蓋,同級生們有的喊著「好熱、好熱」跳入眼前的福島川,有的倒在河堤上重重疊在一起,還有的被住宅埋住,發出悲鳴請求幫助。周圍的房屋全部倒塌,上空塵埃與瓦礫飛舞,落在地上。所有人都被燒傷,河岸上人們緊抓石牆,大叫求助。
原美味
松室一雄
當時32歲
61歲時畫
在哪裏燒掉死去的孩子呢……
背上孩子臉上的燒傷處,白色的蛆在蠕動。撿來的鐵盔,想必是打算用來放孩子的骨頭。
若不走得很遠,就完全找不到可以充當柴火的東西。
【被爆一天後】[...]我握住被壓在校舍下的孩子的手,說什麼「振作一點」,說什麼「是日本男兒就不能哭」,我只能喊點空話。火勢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一處接一處地燃起來,「請救救我!」從地底竭盡最後的力氣叫喊出來,但我只能避開火星逃命而已。
綿岡順次郎
當時46歲
75歲時畫
睪丸膨脹的屍體
神谷一雄
當時20歲
約57歲時畫
寄贈者 神谷タマ子
將負傷的孩子緊急送往江波陸軍醫院的、腸子外露的年輕母親。
神谷一雄
當時20歲
約57歲時畫
寄贈者 神谷タマ子
廣島陸軍病院江波分院。為了求水而把水龍頭推倒、掘洞的人,基本上都死了。
神谷一雄
當時20歲
約57歲時畫
寄贈者 神谷タマ子
有具燒焦的屍體生前試圖幫助一名被倒塌柱子壓住的人。我想她們可能是一對母女。
神谷一雄
當時20歲
手腳骨折,腸子外露的燒焦屍體。
増田節雄
40歲
約70歲時畫
[...]
八日還在喊著「士兵先生請給我水吧」
九日變成了「士兵給我水」
十日只有斷斷續續的聲音「水」「水」(夜裏連呼)
醫師傳達了指示,說如果給水喝的話會加速死期的到來,所以絕對不要給
外行的我看了也知道沒希望得救了
沒有給她一杯水這件事,三十年後的今日我還感到遺憾和抱歉,想到就後悔
※配給的粥一下子就變成了蒼蠅山
水水水水水水水
不停地叫著,絕命
佐野博敏
17歲
「游泳的烤魚」
[...]
清晨,當船開始在太田川河口靠岸的時候,船舷旁有一隻失去背鰭、鱗也被燒掉一半的魚——好像是一條挺大的鯽魚——在水面漂著。伸手去抓牠,牠東倒西歪地游開,又繼續漂著了。那個時候看了也沒多想,後來才意識到那條魚應該是在原子彈炸裂時【註:原文為「原爆炸裂時」】,在靠近水面的地方被強力的放射線給炸到了【註:原文為「放射線に被爆した」】。我的母親在離爆炸中心很近的富士見町的自家被爆、負傷,避難時失去知覺,好不容易作為重傷者被收容。五天後她在坂町的收容所被找到,被禁止活動、要求靜養,似乎反而沒有受到輻射的二次傷害而情況惡化,半年後白血病的症狀也漸漸改善了。在這稍微能喘口氣的時候,對照市內的慘狀,不由自主想到那隻在清早的清澈水流中放任自己漂浮的、活活變成烤魚的、可憐的魚的身影。
切明千枝子
15歲
※出自證言影像
我的妹妹(當時14歲)在現在的廣島站的北口進行工作的時候,我曾從她那裏聽過關於原子彈落下瞬間「極強烈的光」的說法。
她說,七色的光匯成一束筆直地發光、閃耀地昇上天空。她看到後心想「哇,好美。」但是後來她知道了在這道光下有許多市民因核爆喪命,想到「哇,好美」這樣的話是不敬的,就無法跟人說出這樣的話來。
所以被爆後很久我才從妹妹那裏聽來這些話。真的很美的彩虹般的顏色,從地上朝著天空,發著光閃耀著昇起。
切明千枝子
15歲
※來自證言影像
8月6日遭受核爆,家倒塌了。該說是在野外的平地上露營嗎,總之就是在外面睡覺。我後來還會想起那時看到的天空。廣島的天空清楚地分成了兩個,遭受核爆的西北方向,天空是被燒得鮮紅的血色;東南方向,是整片的星空,無數流星劃過。我看到這些,心想,那流星⋯⋯是死去的人們的靈魂嗎,或許是他們正在昇天的樣子。我邊想邊流淚,遠眺天空。我有這樣的記憶。大概有兩晚、三晚都是這樣的狀態。[...]
山田須磨子
當時20歲
50歲/78歲時畫
【第一幅畫大約創作於1974/75年,第二幅畫大約創作於2003年,描繪的是同一場景。第一幅畫的介紹文字較簡略,內容也基本包含在第二幅的介紹中,所以本文只收錄了第二幅的介紹文字】
八月,我弟弟出門去市裏,據說是穿過火海好不容易到了十日市。七日的清早,我和弟弟和去尋找親戚。做了很多梅乾餡的飯糰放在套盒裏,幾乎是扛著帶過去的。回程時,從三瀧沿著河邊走過寺町、基町那一片的各個街道,走過相生橋、橫川橋。然後從基町朝著相生橋來到電車站的軌道。忽然擡頭的瞬間,看到了美國士兵,不知為何心裏一陣抽痛,像是【對方的】心和靈魂的訴求通過呼喚傳達過來了。我感覺到,【對方的】靈魂希望我能將【對方的】死告訴友人、雙親。「就算要傳達,一切都毀了,能去哪呢?」弟弟也說了同樣的事。尋找家屬的人漸漸聚集到這裏,大家都說「做得太過分了」,然後離開。
在電車站的煤氣塔,切了木板做了十字架,兩名美國士兵被架在上面,右邊的那位被鎖鏈和鐵絲纏繞著。右邊的人可能是上司,大陽穴被狠狠槍擊過,兩手被釘子釘住,再用鐵絲纏住。真的是非常悲傷的臉。左邊的人比右邊的稍矮小些,年輕人的樣子,血從頭流到臉頰,用鐵絲綁在十字架上,【和右邊的人一起】並排豎立著。兩人的臉都是青白色的,看起來真的很悲傷,不可思議的是沒有燒傷,也穿著整齊的衣服(國防色的)。沒有一處傷的乾淨的臉【註:原文為キレイ,也有美麗的意思】,是我從未見過的光景。我唯有合上兩手禮拜。
過了一會兒有人來了,我沒法靠近了。那時我想「說不定還有些體溫」,至今還忘不掉。心裏的事沒有說出口,只是「想告訴他們部隊裏的友人和雙親」。我一直在祈禱有一天能夠傳達到,相當痛苦。因為是關於美國人的事,我以為是不能畫出來的,但我想到「如果這幅畫某天被美國人看到了,那份心意也許能被理解吧」,就畫了下來。
為他們造墓的人是很了不起的,我對此感到欽佩。卡特萊特教授訪日,流著淚和家人一起參拜墓地。我沒法做到這樣的事,看著電視,真的很感激,也感到心安。我想士兵的心意已經被傳達到了,合掌。
右邊的人在七、八、九日被暴露在相生橋(腳下),左邊的人(小個子)在第三日的九日從相生橋被運到福屋那邊,受到傷害。
渡辺美智子
女校(縣立海田高等學校)四年級的時候。被動員到現在的馬自達(原東洋工業)的時候。八月十五日中午前,我想是在二樓的食堂。桌椅都收拾走了,地板上鋪著草蓆,有百來名被爆者被安排睡在上面。臉腫得比躲避球還大、脹起來、嘴唇像石榴一樣裂開、發腫。工廠準備了一些罐裝的橘子汁,我們被告知要用湯匙一匙一匙地餵他們,讓他們喝。我也想這麼做,但他們的嘴幾乎張不開,有沒有通過喉嚨也不知道。
臉上塗了油,好像人被放到天婦羅油裏炸過一樣,慘不忍睹。衣服似乎沒有太破,但他們是不是活著,我不知道。每個人臉都差不多,無法區別。
食堂角落那裏,有個女人的胸部受傷流血,十來個受傷的人靜坐著。
我不太會畫畫,沒法很好地表現出來。
大場孝子
三瀧竹林的臨時收容所。
因燒傷割傷奄奄一息的人身上有有蛆
眼耳口 傷口 不管是哪 都沒有人去清除
加川宏
當時16歲
74歲時畫
昭和町西部原本有我的家在,燒過之後的土地上仍殘留著餘溫。我要尋找妹妹的白骨,所以處處挖掘、挪動瓦礫,找來找去沒有找到。回程時,在像道路的地方看到幾具燒焦的人類屍體。我想應該是住在我家附近的人,「可能是○○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