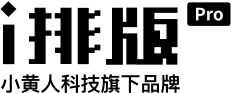文章内容来源于公众号:T 中文版 点此可查看原文。若涉及版权问题或存在侵权情况,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删除处理。
9 月 8 日的北京雁栖湖,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沿着湖岸,远远便能望见水面上停泊着一艘船,白色船身,碧蓝天色,红帆。帆上,“时尚文化大赏”六个字清晰可见。
在大赏的主会场雁柏山庄,“帆”的意象无处不在。红毯的主背板是一面长 9 米、高 4 米的三角形巨帆,见证着 200 多位来宾的来处和远方;红毯的尽头是一艘木船,船头风帆在初秋的微风中轻轻鼓动;遍布会场的指引旗上,每一面都绘有红帆图案,与湖面上的那一张遥相呼应。它们都指向天空,指向前路,也指向本届大赏的主题:还有明天。
为什么是“还有明天”? “不要丢掉希望,”《T》中文版主编李森说,“我们想强调,明天由个体的信念和行动构成,是许多人一起让明天变得可见。”
希望之帆扬满全场,有了帆,当然还要有风。
下午 4 点 30 起,50 余位艺人嘉宾依次踏上红毯。一阵由拍摄团队创造、持续 15 秒的风成为无形而神奇的造型催化剂。薄纱、裙摆、羽毛、飘带 …… 纷纷在这阵“好风”中起舞。社交媒体上,#连风都偏爱 的词条后缀着中国文娱行业最闪亮的名字,回扣了这一创意的寓意 —— 好风凭借力,明天会更好。
于适说,明天是一种“向上”的力量:“我做运动员的时候,教练跟我说,意志、品质(要)不断向上,(那)不是说在你一切平稳安定的情况下向上,真正的勇气是在已经面对挫折的时候,能不能咬牙挺过去,那一步才是真正的向上。”郭柯宇说,“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和明天的观众有更多的拥抱。”井柏然说,他立刻想到了自己主演的《新生》中的台词,“人生不是一场比赛,人生也没有金牌”,他说,因为还有明天,所以更要享受当下。至于刘涛,她的回答充满了一种确定,“坚定自我,充满好奇,吃好饭睡好觉,做个美梦,迎接明天。”
不过,在时尚文化大赏,这些常常站在聚光灯下的艺人并非主角。作为栩栩华生最高规格的文化与时尚盛典,大赏为褒奖本土文化图景的参与者和改变者而生。在随后的颁奖晚宴上,艺人将以颁奖嘉宾身份,将真正的主角请上舞台中央。
谁能代表当下的风向?谁在真正托起我们的明天?经过近半年的讨论和筛选,大赏将目光投向了六个领域 ——
中国顶级高校的中文教育者,从未放弃“批评”,也让“研究”二字与时俱进。他们唤醒年轻人的敏感与思考,让文字成为一种理解世界与自我的方式。“还有明天”是火种的传递,中文之根不会枯萎,吾道不孤。
有责任、有筋骨的中国新闻记者,说真话,问真相,求真理。这越来越难,但难而正确,才能看到“明天”。
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导演,让影像成为提问,也成为回答。他们拍乡村的命运、城市的裂缝、历史的余响、未来的遥望,也拍人的能与不能,敢与不敢,爱与怕。只要还在继续创作,电影就会还有明天。
还在坚守的中国出版人,经由他们看不见的付出,思想得以传递,声音得以放大。重压之下,图书出版正走在它的刀锋处。道阻且长,但图书出版,当然“还有明天”。
出色的中国室内设计师,让今时今日的空间,与心灵尺度密不可分。它前所未有地重要,“明天”也前所未有地呼唤好的设计。
持续深耕的社科研究者,用研究与实践,为历史意义上的明天预言立传。他们真正诠释了“还有明天”的“明天”应作何解:历史没有目的地,但有方向,明天取决于今天,更取决于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向往。
一场亮相,一次致敬,可以对“明天”产生多少改变?尚未可知。但至少,在这一天,在一张张风帆的呼应中,我们相聚,彼此应答,彼此印证。
【分隔线】
下午 3 点起,荣誉得主陆续抵达现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莉带着一卷待校对的书稿来到大赏,原本计划候场时继续校对工作,但在雁栖湖见到许久未见的同行,她忽然觉得,“我怎能辜负这湖光山色。”随后,她便叫上其他中文系教授出门散步了。湖畔,她看见一片栾树林,以及几棵苹果树,兴奋地指给同行者看。
“当我们强调还有明天,隐含的意思好像是我们今天遇到了一点麻烦,所以今天我跟一帮特别优秀的老师、朋友相聚在一起,直面今天的时代现状,考虑文化向何处去。”张莉说。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姗姗来迟。刚落座,他就和教授们聊起了全球文科缩编的现象,不过他强调,“目前所谓的文科危机对我们系没有任何影响。”在黄平看来,中文专业的空间依然非常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对此感慨良多,她穿了一袭绿色旗袍,搭配银色珍珠项链。她和张莉聊起儿子的教育问题。邵燕君的儿子原本念信息科学专业,学了两年之后,自嘲“就是一个平庸的码农”。邵燕君问,你到底喜欢什么,儿子想了想说,还是想学历史。“要是考虑职业的话,就太不确定了,不仅是文科,所有学科都面临着动荡,还不如按照孩子的兴趣来。”邵燕君说,同意儿子调转专业后,“我们俩都觉得大松一口气。”她坦言,她这一代人,经历过历史的动荡,但对未来总是抱有乐观的信念,她笑着问张莉,“明天会更好,不都是我们小时候唱的歌吗?”
在新闻媒体式微的当下,捍卫新闻价值的调查记者显得尤其珍贵。财新传媒的记者萧辉在大赏前夜临时接到任务,被紧急派往了新闻现场,这种缺席,本身也说明了调查记者的职责与常态 —— 在路上。
而如期出现在大赏现场的杨林和李微敖,一到休息室坐定,就分别拿出电脑开始工作。李微敖今年 45 岁,是《经济观察报》的首席记者,他 2003 年入行,是为数不多还在一线工作的资深记者。他至今保持每月 4 篇稿件的工作量,给他私信的人非常多,“我是真的觉得有趣好玩,有新鲜感,不断洗刷自己的认知,所以才一直做记者。”
面对新闻已死的声音,李微敖并不认同。“这里每个星期都在发生世界级的新闻,有太多可以写的题材,也许我们现在天花板越来越低了,但是我觉得,以现在中国记者的水平能力,你还够不着天花板。”
多年不穿高跟鞋的杨林这次穿上了一双 5 厘米的高跟鞋,以示尊重。她也保持每周 1 到 2 篇的报道更新。作为知名商业调查记者,杨林收到过许多公司的高薪邀约,“说实话不是没有心动过”,但是转念一想,“我大一就开始跟着媒体老师实习,大三拿到了《重庆商报》的 offer,那时我才 20 岁,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现在,她 30 来岁,写稿好像已经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条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不好,对吧?我就觉得这一辈子一直走这条路,也挺好。”
杨林是新闻领域五位荣誉得主中最年轻的一位,在获奖嘉宾的的休息室里,原《经济时报》调查报道部主任王克勤对她感慨道,“你赶上了新闻黄金时代的尾声”。 王克勤曾被业内称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虽然已经从新闻转向了公益行业,但新闻仍是他内心深处的归属。“任何时候都需要严肃学科,新闻是有价值的专业,即便是在最坏的时代,依然有人会仰望星空,这就是世界,这就是地球。”他停顿了一秒钟,“也是人类。”
王克勤的这番话让一旁候场的导演仇晟震动,但他当时不好意思接话。颁奖晚宴上,王克勤的获奖感言再一次引发全场讨论:“我认为,说真话,不讲假话,说人话,不讲鬼话,是我要表达的最核心的诉求。”仇晟对朋友说,“这哥们”,他指王克勤,“让我印象深刻。”
青年导演也许是当晚嘉宾中最活跃的。今年 6 月,仇晟的新片《比如父子》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面临口碑争议。他在影院门口摆摊,等放映结束,和观众进行交流。有观众当面罗列了影片的“十大罪状”,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仇晟觉得,能够了解观众的想法,是一次难得学习的机会。
张中臣第一次参加时尚活动,“有点懵”。今年年初,他的电影《最后的告别》终于登上院线,他说,今年大赏的主题,也是他常常对自己说的话:“要有希望地活着,每天要活得很结实。”9 月 19 日,他将携新片参加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对于未来,他相信“有好电影就会有好市场”,今年暑期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张中臣说,他尤其喜欢《浪浪山小妖怪》和《南京照相馆》。
《热带往事》的导演温仕培见到了老朋友孔大山。他正在寻找下一部电影的拍摄主题,每次和不同行业的创作者交流,都让他受益匪浅,“我非常想听张莉老师关于女性电影、女性文学的讲座。”说完这话,他惊讶地发现张莉就站在旁边。孔大山的状态与温仕培类似,也在寻找创作的题材。他搬到了老家,生活平静了很多,《宇宙探索编辑部》后,导演的身份曾让他觉得疲惫,但他现在觉得,未来有机会,还是想继续拍电影。
刚刚在 FIRST 青年影展获奖的导演姜晓萱和《脐带》的导演乔思雪都是内蒙古人,拍的电影都聚焦家乡,她们现在都住在内蒙,一个北部,一个中部。她们一直知道彼此,惺惺相惜,但没有机会见面,在大赏,二人一见如故,聊起了家乡、生活、创作、旅行,当然还有电影。
她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在片场,“还有明天”意味着今天的拍摄出了问题,“我在剧组总是会说这些东西今天拍不了,扔到明天去,好像明天像魔法一样把难搞的镜头都拍好了。”同时这种说法又暗含了希望,“今天拍不完,明天可以继续。”
【分隔线】
在文化嘉宾交谈的同时,雁柏山庄的另一端,颁奖晚宴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的作品,雁柏山庄的设计灵感源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青砖、飞檐和回廊宛如天成般,嵌在湖光山色之间。一条廊桥从岸上延伸至雁栖湖中,尽头是端立于湖面的水殿 —— 当太阳沉下湖面之时,廊桥和水殿就会变身为颁奖晚宴的宴会厅。
事实上,两年前筹备第二届时尚文化大赏时,栩栩华生创始人兼总编辑冯楚轩就选中了这里,想举办一场“非传统”的晚宴。团队当年花了整整三天,用沉静的蓝色配合“业精于勤”的主题,将这里布置成别具一格的户外筵席。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计划,大赏的颁奖场地被紧急转移至室内餐厅。虽然共同经历的这场意外反而让嘉宾更加亲密,但在冯楚轩和团队心中,仍然留下了一个更待明天的遗憾。
两年后,9 月 8 日,团队又站在了同一个场地,这一次,天朗气清。长桌在廊桥上依次排开,“还有明天”的主题,对应的是热烈的红。杭州布料图书馆提供了现场装饰用的所有布料,粉红的布料包裹通往舞台的桥面,水殿的帷幕也是粉色的,桌布则选择了正红,配以红色的花朵。场地设计了 A、B、C 三个分区,有两个舞台,还有一面 LED 大屏,对水殿主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进行直播。
桌花和桌灯有序地就位,身着制服的服务员鱼贯入场,对晚宴的流程进行排演。如果仔细观察,你还会看到一个身着白色防晒服和灰色运动裤的身影,背着包,挂着全场通行证,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快速按下快门。这个“努力不让人注意到自己”的男人,是以率性、幽默和纪实感著称的摄影艺术家冯立。两年前他也曾在这里,跃跃欲试,想抓住一些第二届时尚文化大赏的瞬间,但因为那场大雨,他没能尽兴。今年,我们邀请他再次掌镜。
入夜,VSOP、香槟、葡萄酒都已倒入杯中,嘉宾列席入座。远处的山峦上,蓝色的灯光射向天空。不时有粉丝呐喊的声音从对岸传来。身穿黑色礼服的合唱团开始歌唱,《万水千山总是情》和《甜蜜蜜》,有的嘉宾是老朋友,有的嘉宾是第一次见面,这是一个多姿的夜晚。
主持人李佳念和蓝羽都是大赏的老朋友,两年前,他们和嘉宾一起在这里经历过意外,畅想过未来。现在,当年被临时改为会场的餐厅落地窗上,贴着“明天会更好”的字样,昨天、今天、明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李佳念对着台下的感慨道:“当时我们期许的明天,不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吗?”
冯楚轩的致开幕辞亦感慨良多:“今年是栩栩华生的第 10 年,也是我进入媒体的第 20 年,很多人都了解,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一直在讲,今日事,今日毕,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但今天,我衷心地加一句,今天来的每一个朋友,明天一定更好。”
月亮从树影间升起,是一轮满月,有风吹过。伴着月升中天,荣誉渐次揭晓。岭南古籍出版社负责人肖风华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觉得“非常新奇”。这两年,岭南古籍出版社致力于古籍、华侨图书、港澳学术书籍的出版,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古籍出版年轻化,“这一次古籍和大赏产生连接,能被这么多年轻读者认识,这是对我们古籍的鼓励,为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加大众化的可能性。”
图书出版作为一个传统行业,几次经历危机,但仍坚挺存活,因为书籍是思想的火种,在任何一个时代,人类都需要阅读。新行思的编辑王如菲第一次参加大赏,身上的礼服是她前一晚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可以说实话吗?”她笑道,“这件衣服 100 多块。”
王如菲能感觉到,愿意沉下心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原本可以卖 10 万册的书,现在只能卖四五万,甚至更少,“阅读严肃书籍是一个越来越小众的事情,这确实无法避免。”王如菲解释道,出版编辑能做的是建立小生态,建立一个阅读共同体,“哪怕大浪淘沙,淘到最后只剩一小把,但是这些读者是稳固的,读书的人不可能完全从这个世界抹除。”
尽管行业飘摇,出版编辑依然是王如菲最持久的一份工作,“反而在这份工作里,我感觉到它有很多不变的东西,我也拥有了更稳定的生活,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她说,“泰坦尼克号要沉了,我们也是最后站在船上拉小提琴的室内乐团,我们就做到最后实在做不下去为止。”
奥迪室内设计团队设计总监杜康生是前一天晚上特意从中国台北飞来北京的,他对大赏的印象是,“年轻、文青、时尚”。很多人不知道,杜康生是摇滚乐的狂热爱好者,喜欢看各种现场,“我有一颗年轻的心”,得知自己获奖,他欣然赴约,“正好有一个机会,静下心来回顾自己大半生的忙碌,思考未来。”
历史学家王笛、罗新和医学人类学教授王一方上台领奖时,面对主持人对「明天」的追问,分别从哲学和历史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王一方是辩证的,他形容,明天不是单一答案,而是多元而复杂,“我想借用冰心的话,明天是踏着荆棘流的泪水。”
今年出版了新作《中国记事》的王笛则说:“我们对明天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一定不要失望,一定不要灰心,一定不要认为我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要去拼搏,要去斗争,要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和明天。”
罗新进一步表示:“我们老说历史没有目的地,但是我们又说历史有方向,这就意味着历史意义上的明天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这个方向取决于今天,取决于我们所有的人,取决于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向往。”
作为本届大赏压轴的荣誉嘉宾,三位的话音落下,廊桥下和水殿中掌声雷动。或许在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正共享一种期待:三位教授的致辞,正是我们对“明天”的愿景。
歌唱家毛阿敏从廊桥缓缓走上舞台,合唱团在桥的另一头已经准备就绪,熟悉的音乐响起,“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每个人禁不住跟着轻轻吟唱,这首为迎接 1986 年“国际和平年”而创作的公益歌曲,以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歌词,成为集体记忆,打动着在场的人,带来安慰和希望。
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上,那艘红帆小船从湖中心缓缓起航,为这个夜晚送别,也向未来的无数个夜晚释放出信号。正如我们致敬的长期主义精神,结束,是为了新的开始。
那么,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是“还有明天”?
也许第四届时尚文化大赏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一部分扎根于现实,一部分通向时间。 因为相聚,因为一个又一个仍在行动的个体,我们才敢说,明天会更好。
本文为 T 中文版 原创文章,请扫码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