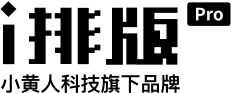文章内容来源于公众号:北京大学 点此可查看原文。若涉及版权问题或存在侵权情况,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删除处理。
去年年底,一位笔名为二姐的作者在“人物”公众号写下一篇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点击查看文章)。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毕业证。在她的印象里,父亲从未向她讲过“名校是怎么回事”,自己也是在父亲患病卧床之后,才知道他曾投身于我国的核事业。
那些和父亲有关的物品
“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它们又无比珍贵。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它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
在父亲脑梗前,二姐与父亲一起生活了数十年,很少想起要去主动了解父亲;而在父亲脑梗后,当二姐想听父亲尽可能多讲讲时,他的语言能力和读写能力却随着疾病开始逐渐丧失。那时,父亲已经无法完整地讲述自己的一生了。
好在还有不少物件可以说话,二姐尝试通过它们来重新认识父亲。
二姐记得小时候看到文凭上面写着“成绩及格”,嘲笑了父亲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
父亲听了只是笑。
他从不向二姐解释名校是怎么回事,也很少讲从一个小县城考到北京是多么不容易。哪怕提起,也是轻轻带过。他说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人物,只是“念书没费过劲”。
半数真诚半数谦虚。从四川长江边的小镇到北京,远不只是2000公里的路程,所有的收获无不依赖于父亲的努力和坚持。
父亲曾给二姐说过,他大学期间为了不耽误时间,常常下课后先在教室学习,等同学们都吃完后不用排队了,才去吃饭。
从高考毅然选择北大,到大学后将外语从俄语转为英语;从在北大学习无机化学专业,到用所学知识服务于国家建设……父亲只是不说,却隐没不去其中那些被克服的艰辛与困难。
二姐看到证书时的第一反应是“我爸业务上还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好像就没有了。直到现在,二姐还不确定特殊津贴是在表彰父亲哪方面的贡献。她对父亲的工作实在了解寥寥。
小时候的二姐也好奇,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和别人的不一样,一周只能回家两次。
母亲也只知道父亲是在保密单位工作。具体哪个单位呢?她也说不准。
“后来很久,我才听说我爸工作的单位叫二机部。”
“又过了好多年,又听说,我爸工作的单位好像叫什么核工业部。”
直到父亲脑梗之后,医生嘱咐要拉着父亲多聊天。二姐才真正第一次听到父亲亲口谈工作。“我小时候你那么神秘。一个星期才回两次家?你干什么去了,你那会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
病床上的父亲比以往更加瘦小了,裹在医院病床上的被子里,第一次告诉女儿:“我是研究核燃料的。”
二姐总是不大能把眼前的父亲和核燃料研究联系在一起,普通的父亲离自己太近了,而国家的核事业听起来又太遥远了。然而,在看到电视上热播的《功勋》时,二姐也会自然地和爱人说,“咱国家两弹一星那么大的事儿,里头有爸一份功劳。”
这个橘色的笔记本是二姐在初中二年级时的新年联欢会上,从父母那里收到的礼物。那时二姐的目光不乐意停留在它上面,而是被其他同学从父母那里收到的漂亮地球仪紧紧吸引。
本子现在看起来已经很陈旧了,曾经作为礼物时,它在当时的二姐眼中也是一样的平凡。唯一特殊的,是扉页上有父母写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这句广为人知的口号,不仅是父母对二姐的鼓励,更是二姐父母一生所思所行的真实写照。
有一次二姐和父母一起去紫竹院公园,路过竹子,父亲忽然问“斑竹一枝千滴泪”的下一句是什么?二姐说不知道,父亲立马接上“红霞万朵百重衣”。
二姐说,之前大家都传,说北大的理科生文科也很好,她还不信,在她父亲这里,她是真信了。
……
再后来,二姐希望父亲还能像那天一样,但父亲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
二姐评价父亲,是个“终其一生,都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他一直在努力把握自己最后的读写与说话能力,他给自己定下了每日任务——抄写一首诗。
字形仍然挺拔,笔画变形的幅度却越来越大,载着父亲最后的努力与不甘。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如往日般坚韧。
往常与非常
“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
在父亲走后,二姐的日子好像和往常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太一样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备忘录轻巧了许多。不用记挂着父亲的服药、换胃管时间了;不用一颗心老吊在手机铃声上了,听见声音就一激灵;也不用总是跑回家探望了,绞尽脑汁逗老爷子说话,还常常不得窍……
但二姐说她不习惯:“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
二姐的心也轻了许多,没有着落,“世上从此又多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还是会有些遗憾,对于父亲的了解不够多。但仔细想想,父亲那一代北大同学们的孩子里,也不乏和自己一样对父亲了解甚少的吧。
二姐父亲是1954年进入北大化学系就读的,由于工作的保密性质,父亲极少在家里谈论他的同事们。
那个年代的北大毕业生们,可能有许多人和二姐的父亲一样,在儿女的童年里留下了亲切却又朦胧的印象。投身于国家建设,他们的位置被锚定在一个个关键却又不得不隐形的节点上,却也遗憾错失了许多和孩子亲密交流的瞬间。直待数十年过去后,他们远离了工作,那段被隐去的经历才能被儿女重新端详。
和往常一样,二姐依旧喜欢“city walk”,轧马路、逛胡同。二姐说,行走是与城市相处的最好的方式。诗不仅在远方,也在眼前,在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努力活着的劲头里。
她爱这种勃勃的生机。
父母在世时,也常常相伴出门。只是年纪不饶人,他们没法像二姐一样walk,就选择坐公交车:夏天五点起床,公交一坐,直奔颐和园。颐和园的花可有得赏,扑簌簌一片,几小时后,公交又给两位老人捎回来。
在家里,两位老人侍弄花草、喂猫。现在,这两项工作也转移到了二姐身上。父母怎么对它们,二姐也不会差了事儿。
“我爸对谁说话都特温和,对猫也是。刚捡来时猫脑门上破了,我妈给它上药,猫就不干,我爸给它上药,那猫可乖了,乖乖的让给上药,特奇怪。我爸那会在家,猫天天要跟我爸睡,睡到我爸脚底下,我爸已经都没什么反应了,那只猫还要跟他一起睡。”
“我妈那会养了一盆儿虎刺梅,那花长得张牙舞爪的,得是我这胳膊左右伸开了那么长,养得特别好。”
今天,从颐和园回来的公交仍旧会照常停在那个站点上。只是,没有照常下车的父母和在车站等待的二姐了。
想念,在每一天
“我妈我爸,还有我最好的那个闺蜜。然后包括我的猫,他们都是我的至亲。我心里特别地想念他们。这件事它经常发生,不用非要等到清明节那一天。他们这些人在我生命中的影响,是渗透到每一天里面的。”
在院儿门口等父亲,是二姐回忆小时候时印象尤为深刻的一幕。
小时候的二姐不知道父亲做什么工作,也疑惑过父亲为什么不天天回家。但这个问题她不常想,更吸引她的,是一些数字——
每周三、周六,父亲会回家一趟;
父亲工作在通州,距离自己住的地方单程公交需要两个多小时;
父亲坐的是大一路公交;
晚上6:55,就可以出门,站在大院门口的路灯底下等待父亲;
父亲的手中一定带着一块义利的维夫饼干
……
那是特意给她带的。
有一次,都七点多了,二姐还没等到父亲,家里人都劝二姐回家等。“我就是不听,就是在路灯底下站着。等到快八点了,我爸才从纷飞的雪花里出现。那天的维夫饼干特别好吃。”
昏黄的路灯和飞舞的雪花,小个子的父亲和更小只的自己,长久地定格在了二姐的人生里。
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二姐觉得他是一个不怎么浪漫的人。
十几岁时,母亲告诉过二姐,父亲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开头就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个人的情意缀在后面。“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
但正是这个不浪漫的人,会在母亲生病后,手抄她喜欢的歌词和戏曲;
正是这个不浪漫的人,会在母亲睡着后,蹒跚着步伐走到母亲床头偷亲母亲;
这个不浪漫的人,总是记得和母亲有关的所有小事,药瓶在哪里他一清二楚;
这个不浪漫的人,数小时的奔波、连日的工作,都不会忘了给女儿带她喜欢的饼干;
这个不浪漫的人,总是鼓励女儿追逐自己喜爱的工作,追求自己喜欢的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不浪漫就不浪漫吧。
温和,才是二姐对父亲的总结:待人真诚、良善,做事踏实、严谨,柔韧性和包容性具在,他对身边人有着最大程度的体谅。
后来有一天,二姐梦到了父亲母亲。
母亲仍然像往常那样指挥着父亲给她理发:“把头发推短点儿。”等二姐追出去,父亲已经推完了头发,基本就比剃秃长那么几毫米。二姐心说坏了,母亲八成又得急,这俩人,一个理发不去理发馆,一个完全不会也敢下手。
二姐想,要是母亲急了,她就告诉母亲,挺好的,夏天凉快。
母亲又和二姐说,专家说吃了某种小西红柿人就情绪不稳定,你爸就吃了,“你看你爸是不是情绪不稳定?”
二姐回:“那是中毒了吧?”
然后二姐就被猫叫醒了。也好,母亲还没发现父亲剃秃了她……
在梦中,一家三口,依然是,一个暴脾气,一个不说话,一个活稀泥。
还像往常一样。
二姐回头,看到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可能那就是思念。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图片 | 受访者本人提供
采访 | 陈之玉、马骁
文字 | 马骁
编辑、排版 | 唐儒雅
责编 | 王嗖嗖
<<左右滑动查看栏目>>
本文为 北京大学 原创文章,请扫码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