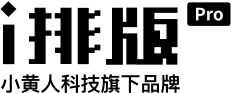一百多年前,人们把看电影叫看戏,将放电影的场所叫戏院,此说法,在港台两地还在沿用。著名电影史学家钟大丰,也曾把中国电影称为影戏。戏又有戏弄、戏耍之意。所以戏的真意,是在不求真的状态下,达到与真实对话的可能,而不必沦为真实本身。这也恰恰验证了电影是最接近人类梦境的一门艺术。
有人说,看戏就是看故事。听上去,有点道理。但真懂看戏的人,是要看亮相、装束。是要听韵白、唱腔。电影这出戏也是如此。中国这 120 年的电影史,就是努力要做出自己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
全世界的电影都有戏味。但之于中国电影更深的戏味,是中国人惯常在集体生活中,才能一起发梦;是同一屋檐下,才方便同仇敌忾;是在共同的历程中,方能取得真经;是要在他人的体认中,才能明确自我的存无。如今看来,中国电影之于「戏」的形态,是衰落了。但戏味,一直贯穿中国电影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历史,成为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由。
所谓戏味,是一个人要遇到另一个人,从而产生情怨和仇隙。中国的戏味,则更是以探询各自的秘密为起点。你是装成男人的女人,你没有你表现出来的那么寒酸,或你也不像你宣称的那样无妻无子,无牵无挂。人物的弧光在于此,人生的真相也在于此。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书写时代的推波、描摹道德的助澜,以及更为不被人觉察的,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一句话,人的愿望一落空,好戏就要开场了。在电影搭建的舞台上,靠自制戏剧情境,在想像性的目光集合中,历代影人各自表演,从叙述不清的历史中走来,又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走去。
由此,中国电影有了这 120 年的惊涛拍岸,并无数次卷起千堆雪。
1895 年,随着《火车进站》的那一列无声的轰鸣,电影艺术在世界上诞生。这西洋景,传到中国,目前可考的是 1903 年,北京天乐共园就有了电影放映。但正规的电影院,又过了两年。也就是 1905 年,在哈尔滨,由一个俄罗斯的从军摄影师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即科普采夫法国电影院。
关于第一部中国自主拍摄的电影,通行的说法,是 1905 年,任庆泰拍摄了《定军山》。但电影史学界对此并没有保持一致性的认同,主要是证据链不足。影像没留存,倒不是紧要 —— 有太多古早的电影都停留在听说过,没见过的阶段。但看片的票根,当年的海报,也遍寻不到。主演伶界大王谭鑫培的友人,后人,包括都没有谈及此事。更重要的,在电影还是默片的时候,为什么要拍一个以唱功为主的戏?这着实令人大惑不解。
所以,也有人说,与其说 1905 年是中国电影摄制的元年,不如说是中国电影放映的元年。
在默片时代,电影更多的时候是个杂耍,是个玩具,跟电影未诞生之前,西方人所热衷的并无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电影的第一主类型,在他们还保持沉默的时候就诞生了,那便是动作喜剧。卓别林也就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电影艺术家(没有之一)。而中国电影也有相应的动作喜剧,如《劳工之爱情》(1922)。又或者以人的肢体运动奇观化的神怪武侠片,如《火烧红莲寺》系列(1928)。后者一度成为票房灵药,在其后的 3 年里拍了 14 部之多,却遭至知识阶层的笔伐。同时,随着审美疲劳的发作,此类刀光剑影,飞来飞去的影像,在市场上也越来越不受待见。
1920 年代,最大的电影公司是明星公司,两位老板张石川和郑正秋皆能编能导。明星公司的创业之作,便是两人联合编导的《孤儿救祖记》(1923)。这部电影大获成功,不仅让明星公司一夜摆脱了初创期的资金匮乏,也让家庭伦理剧,成为中国电影连绵至今,最为重要的叙事密码。但明星公司所标榜的寓教于乐,仍是在封建旧道德的罗网里爬行,与那个思想文化产生大裂变的时代需求相比,像是在原地踏步。
1930 年代,随着左翼电影人的加入,中国电影在精神面貌上才真正做到与时代同步,而在艺术品格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风潮,相信看过关锦鹏执导的《阮玲玉》(1991),会有更为深切的体会。卜万苍、吴永刚、蔡楚生等电影先驱都悉数亮相(包括不太左的费穆)。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导演是孙瑜,在片中,由其子孙栋光扮演。
孙瑜首先是个作家,然后才是位导演。他年轻时,就翻译过杰克 · 伦敦和托玛斯 · 哈代的小说。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导演,在清华大学时,就因写影评获奖,而萌生了在银海泛舟之念。后赴美,在维斯康辛州立、纽约摄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系统地学习了电影的多方面技能。
回国后,孙瑜在几家小公司辗转,后进入后来声名极盛的联华公司,执导了该公司的创业作《故都春梦》(1930),这也是孙瑜第一次与阮玲玉合作。在孙瑜的诗人之眼中,他看到了这位划时代巨星沉郁悲戚的面貌背后,活泼俏丽,更富生命力的一面。按孙瑜的话说,他想拍摄中国女性未受礼教浸染后更为自然的生机。也正是在孙瑜的电影中,阮玲玉不仅仅是当时坊间议论最多的话题明星,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具姿态性的表演者。而孙瑜后来发掘的明星如黎莉莉、陈燕燕、王人美。应该说,更为健康、明亮。当时的女明星大多以病恹恹的体态,如同一个蒙尘的玉器般,等着被人发现,被人擦拭。而孙瑜早期电影中的女性,都自带光芒。与其说她们具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不如说她们更具有一种原始的美,是从天而降,并破空而来。
孙瑜的电影一直关注着一种尚未教化的美,这与他同时期,或比他晚一些的年轻导演相比,都大为不同。不能说,孙瑜的电影没有教化,但教化在孙瑜,只是一个主题性的策略,他更关注的是那些天然,那些能与万物对话的性灵,是蓬勃的生长,然后心满意足的死去。
他不仅从女性身上充分见识到这一点,也从男性身上看到那种因生来自由所带来的力量之美。
《大路》(1935)被誉为中国无声电影的最高峰,也是一卷不失亮丽的掩卷之作,从左翼的立场来看,这部讲述筑路工人的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劳工阶层的群像电影。「阶级对立」和「国难当头」等当时电影最为乐道的主题,自然皆跻身其中。但孙瑜以开阔的画面(摇臂摄影机,业内俗称大炮,也是由孙瑜引进到中国),抒情又不乏激情的叙事节奏,让我们从金焰、张翼、罗朋、刘琼等一众俊男身上,领略到更多的是生命本身,那富于流动的美。而女性形象,由陈燕燕和黎莉莉扮演的角色,也如山茶花般,能自吐芬芳。她们观摩男工在河边洗濯的画面,将永载中国电影史册。这是再健康无比的互望,情趣在其中如浪花朵朵,生命力在其中也如一江春水蜿蜒而去。孙瑜电影的美就在这里,总有一种表意胜过了表达。
本片虽为无声片,但通过影院现场放音的方式,让它有了自己的音乐,那就是有两大音乐巨子聂耳和任光创作的五首歌曲。主题曲《大路歌》由孙瑜填词。电影《阮玲玉》中就有聂耳灵感迸发的惊喜段落。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基本将《野草闲花》(1930)中的插曲《寻兄词》当作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作词还是本片的导演孙瑜。
中国电影一直有苦情戏的传统,最经典的莫过于蔡楚生和郑君里联合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那是国运即人运的双重悲怆,是和平即战争的持续发作。纵观 1949 年之前的中国电影,那些值得被影史一书再书的电影,基本是以现实主义品格为基调,哀民生之艰苦,叹国运之动荡。
应该说,孙瑜也是此阵营的旗手之一。但与沈浮、史东山等同代导演的写实主义风范不同的是,孙瑜的电影有着一定的童话意味,而非一味的与现实持浓烈而深入的关照。他在视听上的自觉性,惟费穆可与之媲美。而他对人非社会性的洞察,是那个年代的电影人,更为稀缺的电影品格。他也会书写时局的动荡,但他内里,悄然关注的是变局中那些不变的,恒定的那一部分。他很少表现彻头彻尾的黑暗,存活于他胶片中的壮男健女,仿佛自有一番天地,供他们驰骋。他对于未来的期盼,远不及他对人之于自然,人即自然的热望和相信。孙瑜在 1936 年执导的一部电影,就叫《到自然去》。
1949 年,孙瑜历经新旧两个时代,所倾心创作的《武训传》横空出世,这部现实与梦境反复交织的人物传记片,标志着孙瑜的导演艺术已经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对人世的思考,具体说人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哲学命题,有了极为清醒又异常痛苦的认知。那个曾经浪漫纵情的电影诗人,进化为扪参历井仰胁息的思考者。一个义丐的命运之所以唏嘘不已,来自他自问教育的结果是不是只能将受欺者培养成欺人者,却不能自答出教育的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还是知识只是命运的一个因子。
这部影片在全国公映之时,曾好评如潮,但很快风向大变,引发了我国当代文艺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文艺论争。《武训传》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在此,我们暂且不去深究《武训传》自身命运的起起伏伏,只说一点,那就是多年后,陈凯歌执导的《孩子王》,是对《武训传》的一次呼应。谢园演的老师是一个盗火者,但能否照亮孩子们的心灵,他并没有太多把握。他只能告诉他的学生们:千万不要再抄了,连字典也不要抄了。这种心灵的孤绝和旷野的空寂合二为一,这个孩子王不再称王,而以远离深山的步态,归隐于更为茫茫然的洪荒之中。
《武训传》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灵魂,也是电影的灵魂。
1958 年,孙瑜执导了他电影生涯里最后一部故事片《鲁班的传说》(之后的《秦娘美》乃戏曲片)。影片讲了三段与鲁班有关的故事,第一段最好,成就了一笔嫁妆。有情人在互望,而鲁班正准备消失在人海。第二段也好,鲁班让没心思好客的人,还得殷勤地招待自己。空间设计上与日本电影相仿,人占据屋内的一部分,留出的另一部分像是在凝视着这位自命平凡实际非凡的大工匠。第三段稍差一些,主要是白了一些,也让鲁班的神秘感散去了一些,但还是很好。鲁班在做梦,梦到花,梦到风车,梦到他走过的山山水水。可以说,他在与他的神思相会。一般电影有此段落时,会有些肉麻,而孙瑜只是推开了窗,窗外便有了桃红柳绿。这是学不来的,看看就好。
三个工程、先后是铺桥、搭庙、建楼。都不同程度的跟神祇相关,后两者干脆就是供人膜拜的。活干得不漂亮,是要杀头的。也就是说,你不会造神,神是不会放过你的。孙瑜在用他最后的叹息,在造他心中的神,他是不强迫人也不打扰人的,并生怕有人会对他有所惦记。这个神最大的魅力,是鼓励我们这些凡人,只要多看,多想,你也会成为神。
孙瑜既拍神的出现,更能拍神的消失,拍神的存在是为了不再存在。他属于草创时期的中国。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他同样属于他不曾描述过的世界。
中国电影的「草创时期」最重要的三大公司,即明星、联华和天一。三大公司的老板不是会编就是会导,要不二者兼得。除了前文提到过的明星公司的两位老板,天一公司的老总邵醉翁也是二者兼得,其弟邵逸夫也做过导演,和著名导演汤晓丹合作过《白金龙》(1933),本片一般被认为是第一部粤语电影。随着香港电影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勃兴,已是最为重要的方言电影。此话题暂搁一边。
且说邵醉翁在抗战胜利后,便将家族事业移交给了邵仁枚、邵逸夫兄弟。此时,两兄弟的事业主要放在南洋。而他们的另一兄弟邵邨人先一步在香港成立「邵氏父子公司」,但在当时更时尚的电懋公司和更激进的长城公司的夹击下,毫无还手之力。1958 年,邵逸夫掌印,并将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于是,一个华语电影文化与产业产生巨大影响的家族帝国,开始了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云覆雨。
邵氏的辉煌期,是以阳刚替代了阴柔,结束了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直至电懋公司的一时风光,所形成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脉络。赤膊上阵的男人,由他们所组建的江湖开始大规模的集体上场,为后来香港电影更为锐利更为深入也更为澎湃的男性叙述发出了先声。
就像中国北京电影制片厂有水华、成荫、崔嵬和凌子风这四大帅,邵氏影业在他的黄金时期也有他的四大帅,即李翰祥、胡金铨、张彻和楚原。就像水华是北影四大帅里成就最高的,李翰祥是邵氏公司之所以能全面崛起之时,最响亮的那块招牌。
与李翰祥在邵氏齐名的另三大导演,皆是中国武侠电影的重要旗手,但印象中,李翰祥从来没有染指过武侠制作。他要拍的还是女人。他的第一部电影《雪里红》(1956),决定了他此后电影的三大趣味,一是女人,二是戏班(严格来说,是戏本身),三是,民间俗情。(当然,他盛名之后,所执导的宫闱戏,是他的另一大趣味。)
举例来说,《垂帘听政》(1983)可以看做是李翰祥三大趣味的集大成之作。李翰祥特别爱描写那些不甘心的女人,《垂帘听政》中,他讲的是叶赫那拉如何成为慈禧太后的故事。再则,他在正史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野史的素材,这在他早年的「乾隆下江南」系列里,已露端倪。李翰祥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剧情更为生动,更是因为他所要表达的历史是想像性机制的产物。说句套话,历史从来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人可以是正襟危坐的史学家,也可以是李翰祥本人,甚至是看电影的每一个人。而《垂帘听政》最好的戏份,是咸丰帝明明抱恙,却强撑病体和群臣一道看戏的段落。几乎没有人在专心看戏,都关心这个衰弱的君主,何时离席,又何时归位。看戏的如此,演戏的戏子也是这般。他们是以揣度历史的方式,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历史。在李翰祥看来,历史就是一出戏。他还曾把自己在《东方日报》连载 3 年的专栏《三十年细说从头》,拍成了同名电影,讲的是拍戏的过程,无非也是一场戏。
李翰祥的把兄弟胡金铨专注于明史,而李翰祥则热衷于清史,尤其是晚清这一块。他更留意的是繁华落尽时的种种身不由己,却又能释放出另一个自己的浑茫与苍阔。一个王朝即将迎来它的未日,而为此所作的力挽狂澜,都是以一蚁或数蚊之力去对付那大象之躯。但李翰祥不为此感到凄惶,但又不以旧时代的谢幕好等来新时代的开锣而欣喜。在李翰祥这儿,时势的无常只是在证明命运的恒常。他那些不好一锤定音的历史观,却成就了他在香港历史即将转弯时,所获资源最多的香港电影人。
有必要说一下,西方电影在叙事上有两大源头,即马戏和戏剧。中国也有马戏,最常见的是耍猴,但不像西方那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于戏剧,在西方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中国很晚才有戏剧,有的只是以唱念做打为功课的戏曲。所以,中国的叙事源头是包括戏曲在内的街头艺术。
街头艺术指的是吃「开口饭」的人。具体便是靠说唱来传达民心民情。中国的旧式说唱,相声、评书的叙事性自不必多说。北方的鼓书、琴书都带有一个「书」字。南方的评弹,带一个「评」字,实际都是在讲故事。个人将这统称为口头文学,更好的说法,自是民间文学。
大陆和台湾的两大扛鼎级导演谢晋和李行,都从民间文学里获得取之不尽的营养,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两位大导演因种种原因,对民间文化的采集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相较而言,李翰祥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学,最为集中,最为尽兴的挖掘者和品味者 —— 这是他对中国电影的另外一个无可替代的贡献。无论精华还是糟粕,他都照单全收,他甚至认为只有在糟粕中,才能提取到人性中那些不可捉摸的面貌。他自觉而积极地从中获取大量营养,并内化为他看待中国人的视角和态度。
民间文学,最能上台面的,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让李翰祥一跃成为华语影坛的翘楚,并让邵氏兄弟雄视影坛的大作,便是黄梅调电影《梁山泊与祝英台》(1963)。这是国人最念念不忘的浪漫,桑弧(《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和徐克(《梁祝》,1994)等许多大导演多涉猎过这一题材,但论影响力都不及李翰祥的这一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港台戏迷,要是不看这部电影,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虽说是靠才子佳人电影成名,但李翰祥从街头艺术取得的真经,其实是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俚俗野趣 —— 那些贩夫走卒,婆姨娘子爱咬耳朵,爱嚼舌根的街闻巷议;那些千里眼、顺风耳在隔墙、贴窗后所听闻出的人间逸事。你不可告人的愿望总得有个出口,众生皆浊,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看到别人堕落,真是比自己堕落还要让人开心。帝王将相是孤独但可能并不终老的庸人,才子佳人是经过包装并随时准备除衫的俗子,都能将那点不好意思变得格外有意思,但也就那么点意思。意思一下就是一个男人拉,一个女人倒,所以叫拉倒。
李翰祥电影中的民间性,跟现在的草根逆袭完全不沾边。他们相对而言是认命的,是既认自己的命,也认别人的命,是能从别人的尴尬、无奈和洋相中,借此获取他人的秘密,好丰富自己本就寡淡的生命篇章。好像是别人在替自己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更好像是越是见不得人,自己才更像一个人。
李翰祥的风月奇谭,有的从《金瓶梅》那里得来,也有的来自外国的《十日谈》,更有从北京的天桥相声中依样画了个葫芦,如侯宝林的一些名段。此类影片,基本是短片集锦,也就是一部影片会讲三个独立成章的故事。也有人将李翰祥称之为世界级的短片大王。
这些影片里,女人的风范是最为显眼的,那些莺莺燕燕都太过体认自然,都不费力地视道德如无物。邵氏的女明星均和他合作过,只是有的要整装,有的要裸身。这其中最大的明星是李丽华,李翰祥未当导演时,和李丽华的夫君严俊有过创作上的矛盾,但应该没有影响到他们此后的数次合作。在李翰祥所身处的时代,他几乎和当时名头最盛的女演员都合作过。他第一次让林青霞扮上了男装、第一次让刘晓庆有了睥睨天下的风姿、第一次让巩俐满口污言秽语(巩俐后来应没有了这样的声势)。还可一说的名字有:胡蝶、归亚蕾、潘虹等。李翰祥还喜欢给演员取艺名,如王玖玲之于叶枫、章家珍之于甄珍、姜昌年之于秦沛。
现在街面上早没了耍把式卖艺的,李翰祥式的电影像是绝了种,但卖艺的实质没有变。 窥私癖一发作,八卦心一摇荡,你又会想起李翰祥所为我们留下的那些飞短流长。
20 世纪 50 年代,二战后,世界影坛有了两次极为重要的电影运动,即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前者从形态上要与我们的眼前所见尽量的保持零距离,后者也有一定的纪实美学,但更追求「一人一个现实」的纷繁局面。不知这是否造成了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亦步亦趋,也在世界很多国家遍地开花,如德、英、日、美、苏。也包括南斯拉夫、波兰、捷克等国。可以说,法国新浪潮是电影诞生以来,最深刻也是波及面最广的一次电影运动,也可称之为是一场事关电影语言现代化的革命。
时间来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当中国电影跟上这股浪潮时,这场一度甚嚣尘上的电影运动已偃旗息鼓。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两岸三地各自掀起的电影运动,让整个世界开始重新打量这个神秘的东方。
率先发韧的是香港新浪潮,由方育平、许鞍华、徐克、严浩等海外学子,给以片厂制、师徒制为主要的创作链条,注入了新的生机。他们的电影主要以平实素雅的写实风格,去勾勒专属香港的夜与雾。鬼马跳脱的徐克早期的作品,也持有他盛名之后所不具备的冷峻之风。但香港新浪潮来得快,去得急。但却引发了香港后新浪潮的花开正盛。许鞍华的副导演关锦鹏、谭家明的弟子王家卫,继续引领着香港电影的风骚。
大陆的是第五代的崛起,也是率先在国际上拿到重要奖项。田壮壮第一个发声,其后是张军钊和陈凯歌,自然也有与他们合作的摄影师张艺谋。田壮壮是往地域色彩极浓的边缘走去,后三位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最具标识性的革命历史,进行再叙述。他们所塑造的是与教科书不尽相同的中国形象,是一个经过反思的黄沙漫天、一个行至罕迹的地广人稀。于开阔处观时间的流逝,于昏暗时看人的出没。但却在天地玄黄中,顿感生命的蓬勃和意志的倔强。正是他们的影像,让许多外人一睹他们从未见识过的传说,一种和他们的生命经验有所重合但毕竟陌生的历史叙述。也正因如此,法国《电影手册》将 1978 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招生,视为改变电影的一百个瞬间之一。
台湾新电影运动是两岸三地浪潮之中,最静水深流的一支,也是灌溉面积最广的一脉。中国最好的青春片都得在台湾新电影去找,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被无数人誉为华语电影的最高峰。张毅的《我这样过了一生》(1985)是对中国女性之存在最温婉的一曲赞歌,王童的乡愁四韵,其中的《稻草人》(1987)、《香蕉天堂》(1989)、《无言的山丘》(1992)基本定义了中国乡土电影的最高成就,其后的《红柿子》(1997)则以哀而不伤的语调,为一个时代悄然送终。
侯孝贤在这里面,是起步最早,作品最多,艺术生命最持久的电影艺术家。他的电影分为四大阶段,且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都要更接近电影的本体,人的本体,甚至有着超然之姿,如同枕着时间的河床,作着无止境的漫游。像侯孝贤这种级别的电影人,其越走越远的步履,在世界影坛也是极为罕见的。
侯孝贤的第一时期,因师从台湾扛鼎级导演李行,他最早执导的《就是溜溜的她》(1980),属最常见的台式文艺小品,侯孝贤能做到的是甜而不腻。等 3 年后,他推出《风柜来的人》(1983),被誉为一下子跳上好几个台阶,让整个华语世界多了一个片种,那就是侯孝贤式的电影。他的长镜头运用,像是等着人来,又等着人走。既等着时间过去,又像是要将时间凝固。这是他创作的第二阶段 ,紧接着是他的台湾三部曲,即《悲情城市》(1989)、《好男好女》(1995)和《戏梦人生》(1993),是以疏离之态,却带来了物我两忘的沉浸感。尤其是讲述布袋戏艺人李天禄的传记片《戏梦人生》,在这部高度去戏剧化的杰作里,谈的还是戏剧,是口述文本、叙述文本、表演文本在互相照应,互相提携。
当年阿巴斯在戛纳看了《戏梦人生》,说它好。回去后一想,岂止是好,简直就是厉害。不好说阿巴斯其后执导的那部《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是否受其惠及,但也是在套层结构里,拓宽了语言的意义,是在交流之外的,另一种无表达的表达,更值得飞扬而去的表达。
好的电影,不是拍看得见,而是要拍看不见。《戏梦人生》就极为神奇的做到了这一点,在这部极其悲苦的电影里,我们是没有什么机会流下眼泪的,不用流在脸上,也不用流在心底。
侯孝贤的第三个时期,最值得一说的是《海上花》(1998)。假如说孙瑜的《鲁班的传说》标志着中国古装电影已入云雾之中,那么《海上花》就是中国最好的清装电影,也是最拔萃的与风月有关的电影。
古人爱把妓女称之为「神女」,究其原因,是因旧时的良人是不便抛头露面的,而花街柳巷里的衣香鬓影,就是要给人看的。她们很多时候要担当交际的重任,生意往来,朝野更替,门第之争,常要在这温香软玉中荡来荡去。《一代宗师》(2013)一开始的场面,说的也就是这个。但这些事的要害均与她们无关,她们像是无心的看客,管别人的人生是怎样大开大合,她们都付之嫣然一笑,有谁兴致一起,便可躲进小楼成一统。神女的神就神在,她们就是要与你的理想,你的目的擦肩。你抱负再大,你还是人。而在神的世界里,你是比她们更快奔涌的流水,更早凋谢的落花。默片的名作《神女》(1934)没有这点意思,它强烈的左翼色彩,让这个为母则刚的故事,最终要完成的是控诉,而非将此职业看作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朵朵浪花,它有载舟之能,却无覆舟之意。真有这点意思的,也只有侯孝贤的《海上花》做到了这点。那点近乎干燥的热闹,像是在催眠。片尾沈小红给下一个恩客烧烟泡的场景,是醉人也是醉己。有趣的东西还在,但再看,却越发无趣。而有情的人,先成为无情的人,才好放下包袱,以方便远足。
侯孝贤这一时期的另一杰作《南国再见,南国》(1996),一部讲述还乡,而乡野不再的影片,多年后,我们在毕赣的《路边野餐》(2015)中还能看到其对电影品格上的延续:是运镜上的亦步亦趋,是构图上的惟妙惟肖,更是南方所特有的湿热气息的呼之欲来。《海上花》是女性的迷失连累着男性的走失,而《南国再见,南国》是男性的恣意行走,所引发的原地踏步。但都是人与时间对话时的僵持不下,而进退失据。
爆发于华人世界的各起新电影运动,有一个共同的母题。也就是寻根,也就是我是怎样被历史塑造成今天这样的情形。在这一点上,田壮壮和侯孝贤都没有从始至终纠结于此。不知道,这是不是两位艺术家,在生活中成为好友的缘故。他们不是从内寻找陌生感,而是向往探索思想的边界。寻根是我从何处来,而他们的电影,越发光彩照人之时,是好奇:我要往哪里去。或更极端一点,来去再自如,也总有白日和朗月相伴。
两人都赴日,拍过他们电影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作品,田壮壮是《吴清源》(2006),侯孝贤则在他的第四个创作阶段,留下了他最令人迷思的一笔,那便是《咖啡时光》(2003)。本片是为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诞辰一百年而作,日本人请一个台湾人来拍,他们电影史上的这位巨子,也足见侯孝贤之于电影本身的重要性,到了何等地步。
小津安二郎后期电影,有一个重要的主题,他认为嫁女儿是一个家庭的莫大损失,女儿也将自己的出嫁权交由父亲决定。《咖啡时光》也与嫁女有关。但两位大师自然有不同的觉知。小津影片里的父亲以被动隐忍的姿态来决定女儿的未来(嫁或不嫁),而《咖啡时光》里的父亲是深知一个人无法决定他人的未来,哪怕是父女之间也不可能。这对父女越是回避交流,越是想交流,一个不敢问,一个不敢说。父亲只能以旁听者的状态实现了对女儿动态的体察。
片尾,多列火车穿梭前进。这像极了安东尼奥尼的《蚀》(1962)那段著名的空境,安公或许是想表明坚固的物质比易碎的感情更持久,而在侯孝贤最为钟爱的火车意象里,火车只是一种机械的循环往复,起点与终点都只是相对而言,对方向不同的人来讲,起点与终点是可以互换的,也可以说,都是暂时的。终点之后还有终点,起点过了又会建立一个新的起点。假若硬要将火车与时间的概念挂钩,那么喝咖啡、煮咖啡,直至更漫长的品咖啡的时光,同样是一种闭环,但这种闭环,但没有出口,但一样具备流动的美。太多人拍过时间的流动,而侯孝贤却总能拍出时间的静止。只有这样,被时间塑造的人才能反过来去塑造时间。这是他的崇拜者,如日本的是枝裕和、美国的吉姆 · 贾木许想做却没有做到的。
中国电影应该是从第四代开始有了代际的划分,主要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来确定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但到了第六代之后,就划不到了。包括陆川和宁浩这样的导演。再往后,我们很难对某个导演会有持续性的期待。
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是,进入到 2010 年代,开心麻花,以及由此分支出的西虹市所炮制的电影,屡屡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执牛耳者,而它们的导演如彭大魔、闫非、宋阳、张吃鱼、吴昱翰(作为演员的他表现不错),并不为人们所熟知。还可以说陈思诚摩下的戴墨、来牧宽,会引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吗?不好说,这是一个导演「消失」的年代。张一白、阿甘、章家瑞有多久没拍电影。 更遑论标识性的作者导演能被人广泛的惦记。在这里,对毕赣也不知该不该抱以冀望。藏地导演里万马才旦倒是创作颇丰,但昔人已乘黄鹤去。余下的松太加、拉华加虽才情耀眼,但创作力均有所减弱。
整体而言,中国电影这 20 多年来,急于与人沟通的创作者,与受众连结的是一时的、经不起考验的情绪,而非挥之不去的情感。有志于作者倾向的导演,有沉迷于将别人的个性当成自己的个性,是越是空空荡荡,越要嗡嗡作响。
香港的电影业呈现前所未有的凋敝,我不知道杜琪峰、周星驰、陈可辛这样已过花甲之年的导演,还能拍多久。我个人自是希望他们能一直拍下去。但后继者又会是谁,谁又能扛起这杆不知还能不能猎猎生风的大旗,我不知道。
台湾的钟孟宏、杨雅喆、萧雅全的电影都尚可一观,但很难形成整体性的气候,好去呼风唤雨。他们的电影总有长不大的人,总对成长本身怀有深深的疑惧。这也让台湾电影长期以来,难有更纵情的舒展。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缺乏对人本体的关怀,有也不多。大多是用感动替代感受,用不约而同的往事洗刷我们自己那些最珍贵的记忆,靠不断的解决问题来遮敝真正的问题。
中国电影走到了今天。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再出现像孙瑜那样将诗情画意化作肌肉记忆,像李翰祥那样将我们最普遍的欲望,不怀羞赧地大白于天下,像侯孝贤那样将天地人融为一体,而不留痕迹。这就像唐诗,大李杜之后还有小李杜,再以后呢。任何事物都有月圆盈缺,电影也是如此。我们只是恰逢电影的平缓期或低谷期,放到世界电影的格局里,也是合适的。正所谓,环球同此凉热。
看电影的人,只能静候。拍电影的,也有着各自的好自为之。倘若能将孙瑜、李翰祥、侯孝贤当作美学理想的化身,我是乐见的,这本身也应是中国电影的大幸。
在此,我们只能寄望在下一个纪念日,我们能把我们自己当作纪念品,送给所有与我们有关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