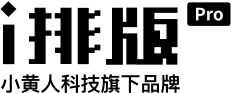它含有更多的赭色,海岸线像轮船底部的弧线那般收敛。马的瞳孔并非标准的矩形,扁平,光滑,深邃,各个角度都让观看者感到平静。沙滩抹上了透亮的黄,天空被重复渲染而略显怪异,成为浮出水面的沉稳色块。他从马的眼睛里窥探到了自己的身影,宽阔的肩膀,收束的腰身,一枚立于方格棋盘中央的棋子,某种尖锐的存在。
这匹棕褐色的马的名字叫“面具”。他取的名字,因为它的额头那抹食鸟蛛般大小的白色印迹,两侧分叉的蜘蛛腿完美地绕开了它的眼睛,像一副面具那般攀附在马笼头划定的区域中央,替代了当卢的位置。
那个下午,他驾驶着一辆两厢斯柯达,沿着景海路奔驰,原定的计划是再行驶上四五公里,便能抵达这条路的尽头,那贯通南北的沿海大通道,他将不得不向左打方向盘,汇入大型货车的车流之中。彩色的货柜总让人充满想象,不仅仅是表面那海浪般的金属外壳,装载的货物可能是云般的布匹、被冰定格的海洋生物,也可能是木制家具,横躺的“互”字形交叠的椅子,或是上下颠倒出无数个“兴”字的桌子。这趟行程的终点在一家外贸公司,可以为他提供更高的职位以及年薪,后者数字令他无法拒绝。
他先注意到的是马的尾巴,在它奔跑的时候不再收束,像被海风吹散的木麻黄叶条,先是细长而笔直,又自然甩出无数个勾状。细看,这匹马并没有跑得很快,缺少真正的腾空时间,四蹄交替着地,慢跑的姿态很优雅。马的躯干始终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让乘骑在它背上的马夫不会因颠簸而过早地感到疲乏。驾驶着一辆汽车经过一匹马,在这座海滨城市的道路上,他觉得是件体验奇特的事。马在这里并不常见。仿佛这是一场人造的速度和自然的速度的比赛,类似的还有飞机与鸟类,船与游鱼,自然造物在人类的科技造物面前没有多少胜算。他在驾驶室里望见了这匹马的脖子,线条分明,就连胸口的肌肉也像岩石一般坚硬,烟囱般的鼻腔喷薄着雾气,有那么一瞬间,他怀疑这是蒸气时代造出的马匹,赛博朋克之马,另一条人类科技发展道路的结晶。其实,这匹马早已气喘吁吁。
马的正脸经由后视镜才被他完全看见,不规则的白色勾连出许多隐藏在他脑海深处的记忆。他在超出几百米之后,选择将车停在路边,拉起手刹,解开安全带,用手肘顶开车门,走出驾驶室。他站在原地等待马的抵达。
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拦住一匹马,仅有的少年时期的记忆也是在马背上,挺直身体,与缰绳保持垂直的状态,让马缓步直至停下来,他很少这么直面这种奇蹄目动物前冲的脖颈。他试着挥手,与其说是对马挥手,倒不如说想引起马夫的注意。马放缓脚步,但未完全停歇,在原地轻踏出微尘。马夫比他想象的年轻,宽松而单薄的麻布外衣,头发长而蓬松,黝黑的皮肤,脸颊被刀削过般,一副略微突出的颧骨。他当然从没看过一个露出诧异表情的马夫,在马背上,他们总是显得如此果断,每个动作都浑然天成。
“你好,这匹马……”他近看这匹马才发现它已显露一副老态,脸的两侧已生出灰白的毛发,嘴角也往下垂,那岩石般的胸口则是突出的骨架。
“是匹老马了,你有什么事吗?”年轻的马夫拍了拍马脖子那片粗糙的皮肤。
“你们准备去哪?”他问。
“原本是去动物园,但他们不收。”马夫说。
“不收?”
“是啊,他们经营也困难,不收老马了,以前都给他们的。”
“你们是做什么的?”
“马戏团,它已经表演不动了。”
“它现在几岁?”他说话的重音落在了“现在”这两个字。
“差不多有二十岁了吧,我来团里的时候它就在了。”年轻人看起来并没有比这匹马年纪大多少。
“相当于……马的年龄跟狗的年龄计算一样吗,七倍还是多少?”他问。
“类似的吧,我也不太懂,师父说,马成年后就长得慢,二十年的马相当于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解释道。
“现在你准备带它去哪?”
“师父联系好了马贩子。”
“马贩子?他们要老马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能转卖给屠宰场?”
“屠宰场?”
“我们也不想这样,已经多养了两年了,实在费草料。”
他试着伸手顺着毛发的方向碰触这匹马的脸颊,追问道:“屠宰场真的会宰杀一匹马?”
“马皮可以做成皮具,马尾不是还能做琴弓的弓毛吗,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么做,当然,马肉能吃,卖给那些餐厅,说不定还能做成马肉罐头什么的,马骨头嘛,蛋白粉,健身的那些人……”年轻的马夫继续打量这匹老马,仿佛还打算补充更多的信息,关于如何分解这匹马。
他无法想象这匹赭色的,胸口还像岩石一样坚硬的马会被宰杀,分割,碾碎,甚至压进一个个马蹄铁罐头里,排列整齐在流水线上接受蒸煮和灭菌,就算是那些被制作成琴弓的部分,被小提琴家在舞台上演奏出多么美妙的音乐,也丝毫不会让台下的观众在脑中复原出一匹马的模样。这匹马从此不在场。
“多少钱?把它卖给我!”他最后说道。
“你要一匹老马干什么?”年轻人表示不解。
“要多少钱,问问你师父,我要买下它。”他坚持自己的想法,沉默了几秒后,补充道:“我认得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面具。”
为自己喜欢的事物取名,似乎是宣示占有权的一种方式。这是他取的名字,在它还是小马驹的时候。他曾以为会一直拥有它,就像任何孩子都有那么一段时间,误以为自己将拥有整个世界。
交易的过程比他想象的简单,马匹的买卖跟车辆的买卖完全不同,没有繁琐的手续,也不用缴纳什么税费,甚至连买卖合同都不需要。年轻的马夫在临走前才想起随身的背包里还有张检疫证明应该交给他。他还需要处理另外两件事,打电话给邀请他面试的公司,告诉他们,他无法按约定的时间到达,除非他们能接受推迟时间,否则将有一匹马出现在公司门口。另一件事是,他不得不通过网约车平台请一名代驾,先将他的车开回家。他骑着面具回到家已经接近傍晚。
在他的想象之中,父亲看到这匹马会激动无比,也可能怀着点愧疚的心情,毕竟那年是父亲亲手将它卖掉的。他也需要感到愧疚吗,他不知道,父亲卖掉马只是为了筹钱支持他上大学,可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上大学是不是自己真心想要的,仿佛对他而言,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人生旅程。父亲会抱住这匹马的脖子哭泣吗,他也不知道,说不定还需要经他提醒,父亲才能想起这匹马的名字——面具,老去的父亲和老去的面具,时间终将带走一切,时间已经带走了一部分。
迎接他和面具的只有母亲,因水肿而发胖,反倒没有让时间在她的脸上划出更多的皱纹。她对他像马夫那般牵着一匹马回到家中,感到不可思议,却按捺住心中的各种疑问,熟练地领着他和面具来到那座废弃的马厩,仿佛这么多年来面具一直都生活在这里,从未离开过。奇怪的是,这座由废弃的集装箱铁皮搭建而成的马厩里,干枯的秸秆堆成半人高,马匹存在的痕迹依旧明显,地面留有干裂的马蹄印,木质围栏上还有被马的牙齿啃过的痕迹,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氨水的味道,跟此时面具身上汗腺的气息极其相似。
“你不是说不回家吗?”母亲用一把密齿叉拨开地上的杂物,为马腾出足够的空间。
“面试推迟了,就干脆回来。”他牵着缰绳让面具在原地绕了半圈。
“在哪里找到它的?”母亲关心另一个问题。
“路上碰见的。”他没有告诉母亲面具原本的去向,只是详细说了交易的过程。
“真幸运呐!”她感叹道。
“是啊,机会让我把握住了。”他看着她提来了一桶井水。
他需要解决草料的问题,面具的牙齿已经不适合咀嚼秸秆,在网上购买的饲料送达之前,他在附近寻找苜蓿草,空地、田野、沟渠,还有一些就生长在路边,这个季节已不开花,仅从叶子锯齿状的边缘可以猜测,大部分是紫花苜蓿。他甚至想好了每天带面具行走的路线。
海边的沙滩上除了随处可见的鬼针草,长势更好的是月见草,还零星开着几朵黄色,它们通常在夜里开放,又在白天收敛,如果有人用手轻碰它们,便会被立即弹射出满手花粉,怎么擦也擦不掉。他不太确定马会吃这种草,只能试着带面具在海边散步。面具总会象征性地啃上几口,似乎并不排斥,也不太喜欢。海水的盐分对马而言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浸泡在海水中,会让马身体里的淡水流失,引起严重脱水。因此,他尽量避免让面具靠海太近,仅仅沿着月见草生长的路边行走,在沙滩的另一侧,更显干燥的边缘。随着潮汐变化,这条柏油路常年接受海浪和沙砾的侵蚀,已经变得坑坑洼洼,还有些渔民会在路中央晾晒刚捕到的,去除了内脏的鱼类,特别是那类常见的蓝圆鰺,背脊一抹海色的荧光,在阳光底下有些刺眼。
沙滩上的铁丝网沿着整条海岸线绵延好几公里,绿色的油漆已经被海风吹得鼓起,并脱落,露出锈迹,有一些碎片没来得及被潮水冲走,扎在白色的沙堆中特别显眼。尽头处有一座庙宇,远远地望去,一对青龙盘踞在半空,翘起龙尾,张牙舞爪,就像刚刚腾云而至,落在屋顶的燕尾脊上。他小时候最喜欢跟同学们在这里玩耍,不在海里游泳或抓螃蟹的时候,就在庙前的空地上捉迷藏、斗鸡、滚铁环、跳房子,玩累了就买一根绿豆冰棍坐在石阶上看海,任凭海风吹拂,只要张开双臂,衣服就会像船帆那般鼓起。
神庙里有位少年正顶着塔骨练习步伐,那是由竹篾编织成的神像,少年的头钻进塔骨的内部,肩膀固定在神像的胸腔内,双手握住骨架,原地来回走动。神像的双手便经由金属构件的勾连灵活地摆动起来。此时,神像还没有披上华丽的服装和头饰,眼睛还被一块红布遮住。
“对,就是这样,幅度不要太大!”一旁指导的男人喊道。
他牵着面具来到门口,立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紧接着是男人持续严厉的呵斥。他认出了这个男人,是他的发小,从小就玩耍在一块。
“在练习吗?”他先问道。
“你回来了啊,啊,这是你们家的面具吗?”男人兴奋地说。
“是啊,我带它回家。”他发现面具很配合地探下脖子,连耳朵也低垂下来。
“多少年了啊,诶,别停啊,继续练习。”
“正月要游神?”
“是啊,每年都有的,忘记了吗,你爸以前还是马夫呢。”
他想起父亲确实当过马夫,不仅仅作为饲养面具的马夫,还参与本地的游神活动,新年的伊始,人们将神从庙宇中请进神轿,走访各个村落,马夫是队伍的开道神仙,模仿马匹的动作来回跑跳,不断挥动手中的马鞭清除路障,在锣鼓和鞭炮的轰鸣声中引领队伍巡游。父亲总在他睡梦之中就已经开始游神的活动,于是,他曾做过这样的梦,游神的队伍都是动物,由青蛙抬着轿子,白鹤吹奏乐器,凤头鹦鹉则骑在马背上敲锣打鼓,他清晰地看见鹦鹉高举着树根般的爪子使劲挥舞木锤,队伍里还有其他的动物,鸡群和羊群跳着舞,猪慵懒地躺在牛背的轿子上哼唱,就连最后面那几只老鼠都举着发光的蘑菇。在梦中,巡游的起点不在神庙,而在海底的宫殿。
“很久没看游神,每年那个时候我都回去上班了。”
“这次也要这么早回去吗?”
“可能不用吧。”他不太确定。
“要不,这次你来当马夫,你还记得这些步伐吧,马夫领头跑可累了,现在这群孩子体力都不太行。”
“谁说的……”正在练习的少年反驳道。
“你练你的,大人说话,别吵!”这回男人责备的声音没那么坚决。
“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我还记不记得。”他说。
“我们都靠肌肉记忆啊。”男人说。
他想起好几年来,每个工作日都被手机的闹钟唤醒,准时起床,开车到公司,打卡,启动电脑,查看需要处理的文件,回复邮件,参加会议,提交工作总结,有时还需要加班到深夜,整个过程需要调动身体的肌肉保持一种僵直的状态,说不定这也是一种肌肉记忆。他很难想象自己居然会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他需要休憩,面具也需要,而且它在马戏团的工作强度肯定超出他的想象。他还没想好他和面具在这段休憩的时间里需要做什么,休憩不需要计划。于是,他告诉发小,离游神活动还有将近两个月,让他再考虑考虑。初回小镇的这两天,他就像个游客那般,带着面具在小镇上四处行走,和童年时一样。
马的眼睛对蓝色和黄色特别敏感,他试着想象只有这两种颜色的世界,类似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经提到的那种逐渐失明的过程:首先失去颜色是黑色和红色,然后剩下三种颜色——蓝色、绿色和黄色,黄色是最后消失的,但现在连黄色也离开我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种棕褐色——一切都很暗淡。他不知道这样的年纪的面具是否也只能看到棕褐色的世界,对它来说,这片漫长的洁白的沙滩是不是跟礁石一样暗沉,亦或是与它自身的皮色融为一体,只是它身体的延伸。它迎着潮气行走,每一步都将填充世界的空隙。
在海边散步的时候,面具很受小孩子们的欢迎,有些游客以为这是某项海边游玩项目,就跟驾驶沙滩车类似,付费,然后获得一段沿着海岸线骑行的时间,途中可以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第一个乘坐面具的游客是个女孩,她没有听父母的呼唤,去乘坐沙滩车,而是拉着他的衣角问:“我能不能骑这匹马?”
他犹豫了几秒才回答:“当然可以。”
“太危险了,”最先赶来的父亲这么说,“又没有头盔、护膝什么的。”
“没关系的,它性格很温和。”他完全可以趁机拒绝的。
“这匹马看起来很老。”女孩的母亲说。
“所以它几乎跑不动了,只能这样散散步。”
“我就想骑马。”女孩嚷嚷道。
“好吧,一趟多少钱?”女孩的父亲问他。
“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让女孩的父亲把女孩抱上马背,并叮嘱她要握紧缰绳,两腿夹紧。他每说一句话,这对年轻的父母都要向女孩重复两遍。
他想起父亲第一次教他骑马的时候,也是这么简单地交待了两句,然后使劲拍打马的屁股。马便朝前飞奔起来。那种带着颠簸的速度令他恐惧,与坐在一辆飞驰的摩托车上完全不一样,马背更光滑,马鞍并非纹丝不动,即使双脚踩着两侧的马镫,使出全身的力气夹紧双腿,他还是感觉自己随时会从马背摔落,迎面而来的风比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来得真切,因为它变得如此散乱,又如此锋利。他已经想不起后来是如何让马停下来的,整个过程太突然,以至于他只能听见自己突突突的心跳声,脑袋一片空白。
他当然没有拍打马屁股,而是一起牵着缰绳缓步向前走去,速度慢到来得及细看每道涌来的海浪。他甚至能看见自己的父亲光着膀子在海里游泳的样子,每次抡动手臂都在抵抗海浪的推挤,那对被阳光晒得发红的肩膀像浮标般,一次又一次地顶开蓝色,钻出水面。他从未想过这对浮标有一天会沉入海底。
夜晚,他牵着面具去往海边的桥洞,底下由路肩打通的人行通道,再往前二十米就是无垠的沙滩和永不停歇的大海。他会带上便携式投影仪和蓝牙音箱,在桥洞里播放电影。刚开始都是一些老电影,他觉得桥洞由石板条构成的墙体有着细腻的颗粒质感,很适合这类电影。后来电影的类别越来越丰富,有时他也会播放动画片。观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镇上的老人和小孩,还有些邻居会提前问他晚上要放映什么电影,每日的电影预告便成了这项工作的一部分。面具也喜欢看电影,闪动的画面似乎在不停地刺激它的视网膜,它在看电影的时候显得特别安静祥和,连呼吸也变得平缓。
冬天的海边没有多少游客,就连本地人也很少迎着冷冽的海风出现在沙滩上。涨落潮的时间每天往后推迟四十八分钟,这种不算明显的差距很容易让外地的游客忽视。与大部分人常识相悖,退潮时的海其实比涨潮时的海更凶险,不少人会选择在退潮时来沙滩玩耍,甚至下海游泳,并不知晓此时的海浪暗含的洄流很容易将游泳者往外推挤,远离沙滩,就算是水性好的人也需要费很多体力才能游回岸上。他骑着面具在沙滩上散步,听见一阵女人的呼救声,便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甚至都没看清呼救的人的模样,就顺着对方指的方向冲入海中。冰冷的海水先是没过了马蹄,接着是他的膝盖,海水很快便蔓延直面具的胸口,他立即从马背上下来,一手抓着缰绳,另一只手尽力去够那名落水的男孩。父亲除了教他骑马,还曾教他如何在海中救一名溺水者,不要正面接触对方,溺水者因恐惧和求生的本能,会死死地抱住营救者,导致营救者无法蹬腿或者划水,那样的话,别说救人,自己也会搭上性命,最好的方式是从背后拽住溺水者。那一瞬间,他想起了这些,便使劲用脚将那具紧抱着他躯干的身体蹬开,在水中重新调整姿势,一只胳膊从对方的背后绕过胸口,插进另一侧的腋窝。在这片充满白色泡沫和死亡气息的海中,男孩、他、面具这三个突兀的点总算连成了一条线,他们努力将脖子伸出海面,一向沉静的面具也发出嘶鸣声,使劲将他们往岸上拖拽。在他和面具耗尽体力之前,他们回到了沙滩上,这三副身体同时用止不住的颤抖庆祝劫后余生。面具的鼻子不再喷薄出温热的雾气。
“它肺部呛进了一些海水,可能有细菌感染。”小镇的兽医这么对他说道,并为面具注射了抗生素。
他知道海水对马的身体的危害,高盐度的海水像海绵一样汲取马身体里的水分,导致细胞渗透压失衡,甚至引起脏器衰竭。他还想起小时候在沙滩上看见的那具搁浅的鲸鱼,大人们纷纷用水桶从海里提水浇灌在鲸鱼的身体表面和嘴里,以保持它体内盐分的平衡,虽然那个夜晚他们费尽了力气,最终也没有挽回那头巨型水栖哺乳动物。马不一样,需要立即全身浇灌淡水,以补充它体内丧失的水分,可惜水温难以控制,母亲烧开了一锅又一锅的热水,将它们掺入冷水中,调配适合的温度,以保证面具的体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浇灌它的身体,让它喝下足够的温水,再用毛巾擦干它的体表。面具依旧瘫在地上,呼吸也变得微弱。他将稻草塞进面具的腹部与地面的空隙,以减缓它体温的丧失。
他和母亲轮流照看,面具的情况并没有太多好转。到了第三天,面具依旧没有进食,他试着喂它一些燕麦。它只是轻轻咀嚼了几口便吐了出来。他又一次请来了小镇的兽医,除了继续注射针剂,这次兽医用盐为它搓洗了舌头,以保证它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又灌了一些药剂。离开之前,兽医也没法告诉他面具究竟能否脱离危险。那些劝他放弃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费这么大的心力救一匹年迈的马,值得吗?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这不需要回答,从那个与面具重逢的下午,答案就已经再清晰不过。
新闻媒体的报道,还有受救男孩的母亲赠送的锦旗,对他和面具来说,都成了某种搅扰。他拒绝了一切采访,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他谢绝了各种救助。他还将自己面试的时间无限期推迟。看着面具那两颗努力睁着,依旧深邃的眼睛,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阴影都已被抚平,他愿意等待面具重新站起来,走出马厩,他还想牵着面具在海岸边散步,在小镇上找寻一丛丛野生的苜蓿草,等待它们开出紫色的花朵。
正月,到了游神的日子。天际刚刚泛出鱼肚白,海岸边的木麻黄树林被风刮得刷刷直响,队伍早已集结在神庙门口。几阵掷筊磕碰地面发出的清脆声之后,神像被请出神庙,紧接是锣鼓和鞭炮的声音。他顶着一副竹篾骨架,外罩墨绿色神衣,头桶上戴着工艺繁复的金银头饰,神像那粉色的脸露出威严的表情。他扮演的马夫手执马鞭,站在队伍的最前端。在这被层层圆形箍住的空间里,他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心中不断默念父亲教他的口诀:腰胯为轴,上体中正,肩沉背松……他舞动起马夫的双臂,双腿模仿马的步伐,灵活地来回跳了起来,仿佛他正骑着面具优雅地缓步前行,手中握住的不是竹条,而是缰绳。马鞭随之在空中舞动,挥向队伍前方可能出现的任何障碍,也挥向未知的生活。
在人群中行进,他更多的只是使劲地抽打虚空。